我小时候最亲密的玩伴是堂姐,她比我大三个月,一个屋檐下长大,是亲戚,邻居,同学,朋友,所以,也是仇人。
我们总是因为一件小事争吵,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就开打,纠缠在一起,奋力去揪对方的头发,挠,抓,抠,扣准一小缝肉,狠狠地掐下去,保管让对方疼得尖叫连连,退避三舍。但打人的事一旦发生,双方家长就会介入,我妈和她娘又要乒乒乓乓干一场,涉及面太大,激发上层矛盾,影响家庭大团结,一般不常干。
主要还是争,一触即发地争,义愤填膺地争。回忆童年时光,不管我的怀旧情绪走到哪,堂姐撇鼻子瞪眼睛小嘴巴嘬得啾圆奋力分辨的表情都会来作陪。
我们争的话题也很小,牛郎星大还是织女星大,蛇精厉害还是蝎子精厉害,你家有钱还是我家有钱。
一个说,你家有钱,你家有电视机。
一个说,你家才有钱,你家有新房子。
一个说,你家有钱,你家有自行车。
一个说,你家有钱,你家每个星期都吃肉。
如果接下来的那个没话说了,就会气得一连半小时都不说话。
六岁以前,我都是最先词穷的那一个,每次战后,都气得跑到猪圈里去打猪,打得它满场飞奔,猪屎飞溅,以至于我妈特别纳闷,潲也吃得欢,怎么这猪就是不长膘?
后来,我发誓要雪耻,闭门一周,苦苦修行吵架术,皇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在第七天早上,我悟了。
从此骂术突飞猛进,几乎战无不胜,几个月下来,把她气得人仰马翻,不敢再进我家的门,路上见了,就像朵蔫叽叽的狗尾巴草一样低着头,遇到什么事,都要怂三分。
这个万马齐喑的绝招其实很简单,就是搬出“别人”。
比如上一个争执。如果我是接下来的那个,就会说,你家才有钱,别人都是这么说的。
在这个强大、神秘、浩浩荡荡、令人毛骨悚然的“别人”面前,堂姐立刻停了嘴,一脸惧色,啊,别人真是这么说的?
那还有假?
谁啊?
好多,至于具体是哪个,你就不用知道了。
有时为了加强表达效果,更有可信度,让她毫不怀疑,我会捏造一些人物、场景、情节(编故事的天赋那时就露了尖尖角),来让她相信。
“真的,前天我去上厕所时,听到里面有人说你,她们说你长得丑,人又笨,都不想跟你玩,我还在屙屎呢,就逼我发誓不要跟你说... ...”
后来,我眼见着她在“别人”的阴影里直不起腰,人变得自卑和脆弱,说话细声细气,走路瞻前顾后,不敢说真心话,更甭提追求真正想要的东西,从小就学会了揣测着别人的脸色过活。
我姑姑是个真性情的人,经常白着眼说她,“金金怎么这么小胆,一点都没朝气!”
那时,我一点也没觉得良心不安,反而天真地以为自己赢了和她的八年抗战,很有一种有志者、事竟成的成就感。
意识到这种行为之可怕时,已经到了十来岁,那时,八面埋伏的“别人”同样侵入我的生活,干涉我的言行举止、思想观念。
这个嗜好将“别人”引入家中的好客者,是我的父亲。这个中年男人,一辈子都在不厌其烦地说别人家的孩子,别人家的老婆,别人家的房子别人家的车,还有添油加醋地转达别人对我们家人的差评。
在那栋80年代的瓦屋,他粗着嗓门,乜斜着眼睛,巍峨地矗在我面前,使用我当初对堂姐用过的招术,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地来攻击我。
你这只蠢货,你是不知道别人怎么说你?
我立刻紧张成一团,既恐惧又好奇,逼他说下去,我怎么了,别人怎么说我了?
我都不想说啊……说你骄傲,说你现世,说你是耻辱,说你什么都办不好,说蠢得要吃药,说你是只贱婆子,说你差得要哭,说你撞多了恶,说你一事无成,说你是垃圾……
他滔滔不绝地说着,年复一年地说着,直到现在,他仍然使用这种语言和我对话。
年少时容易受心理暗示,在这些刻薄的字眼,和“别人”的轻贱鄙夷中,觉得满世界都是敌意,唇枪舌剑,白眼口水满天飞。于是特别痛苦,厌学厌世厌弃自己,觉得活着本身,就是一种无期徒刑。
这种被社会所排斥的不安全感,我很久都未能消除。做一件事情,首先考虑的是他人的看法,我这么做,别人会认可吗?别人会觉得好吗?战战兢兢地活在他人的注视中,他人的评价体系里,他人制订的陈规褴俗之下。
好在后来终于倔强,放弃跟从庸众,放弃讨好低级舆论,一意孤行地,只想做好一件事,只想对自己负责,再不管“别人”说三道四,七七八八。这样一想,反而自由了。
萨特写过一个《幽闭》的哲理剧,讲他人的关系、禁锢和自由。
戏剧设在地狱的密室中。密室里没有镜子。没有了镜子,人就只能把他人当作镜子,通过他人来认识自我。三个主人公都是有罪者:加尔散是个可耻的逃兵;艾丝黛尔是色情狂和溺婴犯;伊内丝是同性恋者。地狱里没有刑具、烈火,唯一折磨和约束他们的便是他们互相的关系。他们互相折磨,勾心斗角,都不能获得解脱和自由。
“何必用烤架呢,他人就是地狱。”
这句话无比准确地说明了“他人”的可怕,就像一道枷锁,奴役自由意志,强迫我们做出违逆自我的决定。比如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,一定也上了不喜欢的学校,干了不喜欢的工作,买了不喜欢的衣服,说了有违内心的话,归根结底,都是被“他人”所支配,想顺从,想讨好,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和称赞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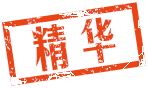
 关注公众号
关注公众号 微信客服
微信客服 小程序
小程序